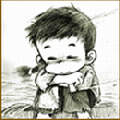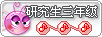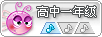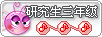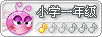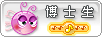不过,六百年后的今天,所有的荣光都掩盖不住一个巨大的感慨: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西洋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庞大舰队,为什么没有为中国开辟一片广阔的殖民地?哥伦布的小小船队可以把西方带上了船坚炮利、富甲天下的道路,为什么郑和宏伟的大洋探险却没有为中国开启工业革命与近代化的大门?对明帝国而言,西洋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上耗费中外无数学者心智的问题,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凿不疑的答案,笔者亦无意再添加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我们也应该反省:这样的提问方式有无事后诸葛亮的嫌疑?毕竟古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都与今人大不相同,站在明王朝的角度,她是否得到了她想要的?对于渴望重振雄风、和平崛起的当代中国,宣扬郑和远航的和平精神是否有助于安抚其它国家的不安情绪?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放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桎梏,把目光放回六百多年前。派遣郑和远航西洋的永乐皇帝朱棣声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显然,在朱棣看来,他统治的地域与人群在理念层面应涵盖整个世界——尽管他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宽。永乐大帝自视为宇内共主的理念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政治伦理,这种伦理早在春秋时期便在《诗经》中经典性地表达出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尚书》、《周礼》等古代典籍中,思想家、政治家们更加详细地刻画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天子居中,统御八荒,其亲辖的方圆千里之地,称为“王畿”,其余的臣民,根据与天子关系的亲疏以及所尽义务的不同,围绕天子排列成一个个相距五百里的同心圆,分别被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等。实际政治实践当然不可能呈现出如此完美的同心圆结构,天朝的统治者们根据缴赋、应役与朝贡情况,对复杂的同心圆层级结构进行了简化,将天下分为“化内”、“羁縻”、“土司”、“外国”等,但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辉普照之下。这种层级性的、一元中心的秩序迥异于主权独立、疆界分明、一律平等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但它却蕴含了一个天下太平的梦想,处于中央的国家,其统治者即天下之主,他必须以德服人,怀柔万方,绝不应穷兵黩武。正如明代宫廷宴飨时所唱的《殿前欢》所云:“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
这种绝不以强凌弱的天朝风范在面对海洋时尤其表达得淋漓尽致。尽管较之中国西部的高原雪域,南部的险峰深壑,西北部的茫茫戈壁,东方与东南方层波叠浪的海洋未必更加险不可渡,但在中国的帝王们看来,海洋与大陆意味着两个性质迥异的世界。翻开中国历史,中央王朝陆上扩张的刀光剑影随处可见,而海洋方面,除了元王朝对日本的远征外,其它主动进攻的例子极为罕见。朱棣的父亲,明帝国开国之君朱元璋语重心长地为他的子孙们开列了一张“不征诸夷国”的名单:琉球、苏门答剌、占城、真蜡、西洋国 爪哇国……,对它们决对不允许主动兴兵讨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不征之国”全部横隔着茫茫大洋,内陆诸国榜上无名。
朱棣正是在传统政治伦理的熏陶之下着手实施远航西洋壮举的。他深知,一个圣明君主应发挥体现天朝风范的“王道”折服宇内诸国,达致万邦来朝的局面,东征西讨,攻城掠地等超出国家安全之外的的“霸道”则应予以杜绝。正如他所自诩的,“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
永乐三年(1405),载着朱棣的野心与抱负,郑和的舰队出发了。这支十五世纪最强大的海军,七下西洋,没有占领过别国的一寸土地,纵横万里,为的只是宣谕明朝皇帝的诏书,向各国国王颁赐银印、冠服、礼品,鼓励他们遣使入明朝贡,并在某些地方树碑以示友好。天朝上国的风范确实折服了万里西洋上大大小小的国家,无数的外国使节甚至国王、王妃、王子纷至沓来,虔诚地匍匐于大明天子的脚下。永乐二十一年(1423),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勃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同时至京,天下共主、一元中心、万国来朝,都在这一年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
西洋,一群“不征诸夷国”,一个大明天子圣恩普照的地方,一个天朝风范的最佳展示之地……,郑和远航西洋的壮举,在实践上把传统中国古老的政治理念前无古人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六百年前的明帝国,已经得到了她所希望的一切。